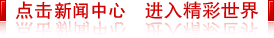歙砚“庙前青”的历史
歙砚石品,林林总总,其中尤为名贵、稀缺和神妙者,当数“庙前青”。此类歙砚通体青碧,宛如绿玉,呵气生水,温润细腻,在当今的古砚收藏者中闻名遐迩,但在悠久的砚史上却有一个逐渐被发现和认知的过程。也许,对“庙前青”的考索探微,迄今还没有终结。
早在北宋,随着以婺源龙尾山为中心的多处歙石矿峒的开发,时人已将歙砚列为海内名砚。在诸如唐询、米芾、高似孙、苏易简、唐积等所著砚谱和苏轼、黄庭坚等的诗文中,对歙砚的各种石品(金星、眉纹、罗纹、涮丝等等)及其细目,已作出了较为准确的分类;其时虽然也有人注意到以苍黑为基色的歙石中,偶亦有色调青莹者,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没有出现“庙前青”的概念。在宋代士大夫的相关著录里,似只有曾知青州唐询描述过此类青砚的特征。曹继善的《辨歙石说》转引其文云:唐在金陵同僚处曾“见一砚,方四五寸许,其色淡青如秋雨新霁,远望暮天;表里莹洁,都无纹理,盖所谓砚之美者也。云得于歙,不知出于何坑,今不复有。”大概是这种石品的稀少,加之唐氏“今不复有”的权威性论断弱化了时人的期待,相关青莹歙石形质的细腻素描在此后的著录中颇为鲜见。直到清康熙年间,歙人汪徵远才又有述及。他大约研读过前引文本,在其《龙尾石辨》中用与之雷同的笔法写道:他曾从友人处得一黻字古砚,“石色淡清,亦如秋雨新霁,表里莹洁”,“乃知龙尾之精以色青肌腻为贵”。汪文较唐文进一步提出此石出于龙尾,但仍未予命名,并以“色青肌腻”概括出其基本特征也未提及其产于龙尾山何处坑口。
据笔者有限所见,“庙前青”的概念始于近代徽州藏家,而对其形质加以明确界定的是当代已故砚史专家李明回。李氏在1980年代出版的《中国安徽文房四宝》中提出:“歙石似黑实青,佳者透绿,呈青碧色,其通体青绿者,为‘庙前青',是歙石中之珍品。”据此,他认为前述两砚都可以断定为“庙前青”。
“庙前青”到底出于何处?有一个古老的传说:龙尾山中“庙前坑”。此说首见于文献者大约是清代官绅徐毅的《歙砚辑考》。徐氏于雍正朝中举,出任新安卫,后协助安徽抚臬、徽州知府等办理乾隆朝的贡砚事务,对歙砚多有评述。其书称:庙前坑在罗纹山(按指龙尾山)古庙前,石如紫玉色,间以金星,宋景祐时取石数块,即迷失其处,至今失传云云。近现代以来徽州等地的砚史研究者据此记载及收藏实践,多倾向于神庙说。如认为“庙前青”乃“庙前坑”之讹,而此坑由于并出青、红两色砚材,故与徐氏所录“石如紫玉”相合;1990年代初,人们在龙尾山口附近找到了长期“迷茫莫辨”的神庙旧址,使奇石珍品再现于世。这种“发现——迷失——再发现”的砚史叙事,辗转相传,似成定论。
按徐氏《辑考》勾稽古史,爬梳逸事,长于博闻而短于求证。书中关于景祐年间(1034-1037)采石该坑的记载可能接近于史实,当时唐询(1005-1064)正近而立之年,其入仕成名,著书访友,在金陵得睹“庙前青”,似可作为旁证。但该坑是否首发于景祐,目前尚无从证实或证伪;至坑后是否确有“神庙”,是否采石数块即神秘地“迷失其处”,以至下延数代俱无踪可寻?则其中疑点颇多,尚可探究。
一、笔者曾两度到龙尾山采风,颇觉神庙说似嫌牵强。“庙前坑”遗迹地处龙尾山阳的古坑群落之中,东去百五六十米许即为砚山村口,其坑址地势高出山下芙蓉溪仅约二、三十米;其旁三十米许,为与之平行的眉纹中坑,以及逶迤而下的罗纹坑、水舷坑(当地称金星坑);南面隔河相向,为砚山村水口左近的水蕨坑(当地称黄皮坑)。“庙前坑”矿面较小,板层不甚稳定,近年小批量出产过青、红两色石料,也有两色相杂,或青底黑带者,故村民习惯称之为“玉带坑”。历询当地砚友,俱称此坑近年开掘殆遍,实为废墟,无论砚山石工或前来考察的歙砚研究者,都没有在这里发现过“神庙”的任何文化遗存。按徽州古俗崇拜多神。神庙是乡土历史的表征,村落兴衰的标志;且其地处水口要冲、村路一侧,周边矿峒遍布,而单谓此坑出石即佚,似不在常理之中。故“庙前”一说,尚可存疑。
二、青莹歙石虽然稀缺,但自宋至清,历代都有少量“庙前青”(或“庙前红”)歙砚传世,并非北宋时乍发即失,“今不复有”。仅笔者经多年搜寻,即分别藏有此类旧砚计三方。其一为南宋砚,纵21厘米,前宽13.5厘米、高3.5厘米;后宽14厘米、高4厘米。变形蝉首池,顺水流淌式,砚堂微鼓,四侧内敛,桥梁抄手。通体青绿,间有苍青色“玉带”,金星少许。询及当地砚友,据称龙尾诸坑中,只有玉带坑(即“庙前坑”)才出这种石料,其底色多为浅灰,佳者泛绿,带纹苍黑,而通体深绿者绝少。可见该砚当出于此坑,且具有“庙前青”石品的重要特征。
另一方系典型的明代早期作工:纵24厘米,横15.5厘米,高5厘米。淌水形,抄手式,修长敦厚。落潮处精雕鲤鱼化龙图。砚面左部约三分之二色青碧,右小半部色暗红;背部通体深绿,诚如唐询所言,表里青莹,都无纹理。其色泽与近年开发的“庙前坑”青红双色砚相同,而其质地更为纯净空明。惜乎传世日久,砚面右半部残损,其残破处红色片岩细密精致。
又一方应为清三代制砚:纵20.7厘米,横15.2厘米,高2.8厘米,较明砚制式略宽而稍薄。平堂月池,四周浮雕松石流云作拦水线。色淡青,背部冻纹两条,如雷电闪于暮夜长空。品相完整,大器可观。
这三方砚,其色泽纹理略有区别,但都具有通体青碧、晶莹如玉、若见肌里的石品特征,符合李明回先生关于“庙前青”的界定。另安徽省博物馆也藏有定为乾隆年间的“庙前青歙砚”一方,更属龙尾之精。可见自宋以降,历代都有“庙前青”歙砚小量问世、有序传承的物证。
三、经笔者对当代“庙前青”、“庙前红”开发过程的跟踪调查,也获得了晚近百年内外,“庙前坑”仍在断续出石的实证。该坑在当代得以确认和经营性开发,得益于原徽州地区及婺源县不止一代歙砚研究者的努力。据笔者所知,近代徽州古砚研究者许承尧、曹一尘先生,在著述或口述里,都叙及、称扬过“庙前青”或“庙前红”。李明回先生据此著书详细介绍,提示世人“勿使此异品沦没”。至1980年代末,海阳歙砚研究者郑国庆先生循前辈线索,几经调查,率先在砚山村翻拆的老屋房基中发现红色、杂色和青红双色(时称“彩带”)的石料,经研究对比,循石索坑,终于在前述村民称之为“玉带坑”废墟中找到了与前人文本记载相符的实物留存。
据采访调查,这些老屋大率建于清末民初,距今不过百年左右。唯1980年代前,当地石工多以金星、眉坑诸坑石材为上品,“玉带”石也较受重视,但不识“红石”或“杂色石”发墨利毫,故致此类石料或弃于河滩山谷,或用于屋础坝基。历史上的文本研究和当地田野开采的长时段脱节,造成了古坑迷踪的假象。
综上可知,徐毅《辑考》中的那一段叙事是一种传说,也可以讲是一则“神话”。歙石历经十亿年沧桑,得日月之精华,藏神秘之林莽。宋唐积《歙州砚谱》中,记载了当时石工具牲祭神、斋戒入山的古俗。前人著录也不乏歙石有灵的神话:或坑上显五色云气,或床下出夜光之石,或撒草化鱼入地挖出良材等等。按神庙出石旋失说,亦在暗示山川之灵性莫测、歙石之出神入化,故同属于神话范畴。只是由于其表述相对人文化和历史化,因而容易为后人所认同。
如上考析,并非否定此说的文化价值。如同人文学科中各种专门史一样,砚史在其漫长的演进过程中,也会因人们种种不同的经历和需要而发生叙事基调的分叉:经验(感性)的、神话(灵性)的、考据(求真)的,等等。这类经历和需要(或者说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广义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发生的种种不同的言说,都有其特定的发言位置和文化取向,因而也都具有存在和传播的正常性。它们从各个角度,共同编织和丰富了悠久的歙砚文化史。不过,对于有关歙石的神话传说,与其将它们作为砚峒起源及其历史脉络的证据,不如把它们视为评判歙砚的价值尺度。这类神话的文化含义,在于用神秘烘托珍贵,从而表现并提升了人们对于歙石及其所在山川地理、人文历史的珍惜。在这个意义上讲,砚史上的神话,乃是古代的采石、用砚和爱砚的人群,出于对文化或者环境的体认感受而在抒发自己的内心世界。
从神话返回实证,笔者有一假设:若按石品结构分类,似不必把“庙前青”限于特定一坑。歙石矿脉异常复杂,层层分剥,品色互异;咫尺之隔,石质常幻。米芾《砚史》述其少时见一砚,“绿如公裳而点如紫金”。徐毅《辑考》推崇眉子,并以其中“石色青碧、石质莹润而纹理匀净者尤为精绝。”据此,前砚可能产于金星坑,后者则明显出于眉纹坑。李明回先生前书认为,徐氏所论“也是指庙前青”。如果把“色青肌腻”、“纹理匀净”作为“庙前青”主要标准的这一立论可以成立,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凡在龙尾诸峒中发现的青碧晶莹之石品,皆可按习惯话语泛称之为“庙前青”,更确切地说,可以界定为“龙尾青”。只是这种佳石即使在“庙前坑”中亦含量稀少,故弥足珍贵。
本文按实证、名物、释义的思路,试图对“庙前青”的历史脉络和人文含义作一新释。其旨无他,仅供同好者讨论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