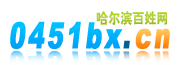|
||||||||
|
|
||||||||
|
 |
当你看到这篇报道时,他们仍然是群租者,在高校周边高层小区的群租屋里:一间使用面积不到60平方米的房子,被刷满石膏的5厘米厚木板切割成七八个不足5平方米的隔断间,每个“房间”基本只能容下一张床。最初,那里住满了备考生,后来,越来越多求职毕业生挤了进去;再后来,是白领与农民工。不明来历、不同身份的陌生男女混居在一起,在体面的楼群里过着难以体面的“新蚁族”生活。
一个月前,新晚报记者住进一间群租屋,开始记录他们的故事。彼时,全国房租继2010年以来已连续44个月上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要求以化名出现,只接受自己的租屋被拍照。我们同意了。与其说是保护,不如说他们是千千万万个“新蚁族”中的一份子,不必被姓名、样貌与身份所界定。
“女汉子”
他们对这种生活并没有什么不满,唯一的问题是清晨难以起床,因为完全意识不到天亮。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最贴切的形容词应该是“阳光”,而很多人却说自己每次从小屋里钻出来,最不适应的就是“阳光”。
“谁的屁股这么大,把厕所给堵了!”
我们住进来的第二天,便被“女汉子”在清晨6时来了个声嘶力竭的下马威。
厕所不是我们堵的。因为一时难以适应,我们拘谨得连厕所都不会上了。
为了采访与记录,我们用于体验群租的这间小屋不足5平方米,只放一张单人床和一只小柜。它占据了芳洲园的高层公寓房小小的一角——可能是原客厅的一部分,现在却被厚约5厘米、涂满石膏的木板隔成独立封闭的空间,距厕所不到两米,关上屋门也能闻到它的“重口味”。
客厅常常漆黑一片,头顶是几根悬着的粗电线,墙壁架子上放着一只闪着灯的路由器。纵使是新建小区,灰暗的房子却弥漫着股股潮气。就这样,和其他8名男男女女一起,我们开始了“集体宿舍”生活。
据说,每次有陌生人进住,“女汉子”都会不满。她身材矮胖,声音粗得像个男人,可能不到30岁,职业不明,性格敏感。她在这里住了两年,这让她的地位独一无二——负责接待所有准备租房的看房者,负责管理“室友”,为他们早上使用厕所的时间排序。被分割得迂迂回回的60平方米房子里,她的屋子是所有群租者最羡慕的:入门后拐进一个L型的狭长走廊,很僻静,关键是有窗。斑驳的墙壁上贴满地图和便利贴,大床上的小书桌摆放着苹果笔记本电脑和茶杯。包裹廉价花布的被褥上堆满了衣服、高级化妆品和一小只煮面锅——有一种拥挤的、奇异的寒酸和不搭配之感。
我们只在第一天得以进入她敞开的房间,随即便被她“拎”了出来。因为是后来的,我们被排在起床第一个使用厕所,时间为“清晨6时至6时10分”。
在这片被戏称“黑大D区”(黑大校本部有A、B、C三个区)的住宅楼里,群租房最早被用作“考试屋”。如今,这里所有群租屋内的生活基本类似:考研、工作、待业、实习生、外来打工者……不同身份的男女交替混住进来,大房子被切割成十几个“蚁窝”,有的甚至将原阳台和厨房也做成隔断出租。每个人的生活空间被隔成四五平方米,却并没有将彼此的生活分隔开来:房门大部分用的是球锁或明锁,一踹就开;男的光膀子在屋子行走,经常有人上厕所不锁门,甚至有人在自己三四平方米的房间里做饭。每天清晨,伴着拖鞋声、叮叮当当的廉价脸盆碰撞声在黑暗中起床;晚上,洗澡声、音乐声、键盘声、嗑瓜子声、电话铃声、呼噜声交错在一起。
我们的同屋林鲍鲍,几个月前犯了头疼病。这种“点把火就能着”的房子里,只要人没睡觉,小屋的灯和门就一定得打开。即使外面有陌生人走来走去,为了通风,认了。但一到晚上睡觉,无论多热都必须门窗紧闭。林鲍鲍终于忍不了了,房东便在她的门上方开了一个“牢房窗”。她勾着手指,拉动“吱呀吱呀”的小窗说:“呦,我的房间变3.0豪华版啦!”
蚁族3.0
他们绝大多数是“80后”,从事服务行业,月收入两千多元,工作不稳定,很多人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高知、弱小、聚居,还往往在廉租房、公租房等住房保障人群之外。
“住这种地方怎么了?”在福顺尚都一间群租屋里,范欢欢反问我们。她在这个高层楼脚下生活了一年,不断帮房东推荐房子的“卖点”:安静、干净,人不杂。
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成了“新蚁族”。
林鲍鲍毕业两年,在一家商场做销售。她管自己叫“蚁族3.0豪华版”。在她的概念里,真正的“蚁族”应该在北京城乡接合部的唐家岭——那是最早在北上广媒体中被曝光的、生活条件十分悲催的“蚁族”。
后来,唐家岭改造,大批“蚁族”被迫搬离,但他们并没有进城,而是迁往比唐家岭还远的村庄。理由很简单,那里和唐家岭低廉的房租接近。
还有一部分人从中慢慢分离出来,“升级”到楼房群租屋里。我们在“黑大D区”里就发现了大量这样的“新蚁族”——他们聚集在四季芳洲、芳洲园、西典家园、征仪花园、英伦名邸、福顺尚都、日出印象、测绘局小区、龙博名苑、盟科涵舍等高校附近、近年新建的中档小区,那里交通便利,有电梯和物业管理,房间能洗澡、有宽带。
听起来相当体面。“私密空间”是这种“体面”屋子最大的卖点,其次是350元至900元不等的租金,包水、电、网,可以每月一交。租房客可以来去自由,甚至不用签合同,也不用看身份证。
目前,北京正严格限制群租,并已于今年7月出台规定: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少于5平方米,每个房间不得超过2人。限制群租的最重要原因是安全问题。而对“蚁族”来说,安全固然重要,钱更重要。
在龙博名苑新建高层中,我们见到了“房东”桂松伟和他怀孕7个月的妻子。一年前,他们将这套新房租下来,隔成6个房间给大学生、白领、护士和农民工,自己则住在没有窗子、仅四五平方米的仓库屋里,结了婚,准备生孩子,在这里长住下去。
“这里不是天堂,可也不是地狱。”林鲍鲍说。
单身公寓 15室0厅
这个一身工人扮相、长得有些“着急”的80后男孩儿,已经是同学眼中“拥有18套房子、身家二百万”的“大老板”了。他的“发迹”,靠的正是群租。
我们的另一个同屋苏杨马上就要搬了。在林鲍鲍看来,苏杨的群租生活“升华”了,居然住上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盟科涵舍。
并不是所有群租者都能“华丽转身”。“那种房租至少一千元的房子,给我只要五百元,跟这儿价钱一样,条件还比这儿好。”帮到苏杨的,正是他大学时最看不上的同学张俊龙。
在盟科涵舍一间空荡荡的新房里,张俊龙和其他4个男孩儿正在为每个散发着石膏味道的崭新隔断房安床。“既然是苏杨介绍的,一个月800元,房间随便挑。”他对我们说。
10年前,大学毕业的张俊龙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牡丹江老家的父母就给了他一笔钱,在四季芳洲买了套房子。“一个人住挺没意思的,我就把房子租给两个考研的学生,后来又干脆把房子用木板隔开,租给5个考研的,那年赚了三万多元。”
第三年,张俊龙一口气从邻居手里长租下5个房子,打成隔断房群租。直到近四五年,四季芳洲等黑大附近条件较好的居民区里,群租已遍地开花。“别看我大学学习不咋的,但我抓得住‘机遇'。当年这附近啥都没有,现在成宝地了。”张俊龙说,“这一行还是有赚头的。七八年前,四季芳洲每平方米1700元,没人买;现在,每平方米一万七,根本没人卖!”
这个80后男孩儿瞄到的另一个商机,正是群租者的“面子”心理。于是,他将目标锁定黑大附近条件较好的高层。从开发商那里,他拿到了部分闲置毛坯房房主的联系方式,以“做仓库”为由,以千元左右的价格长租3到5年。然后,他带着四五人的“工程队”,为新房设计图纸,用最科学的方式打出带窗、通风、有合理空间布局的隔断,放进大床,连好高速的网线。“这里学问最多,要是设计不好,房子是要贬值的。”
“你设计过最牛的房子是什么样?”我们问。“单身公寓15室0厅。”他说,“把一个不到70平方米的房子‘切'没了……”
从毛坯到可以出租,至多需要5天。张俊龙在“58同城”等网站上以“经纪人”的身份滚动发布信息,再找人在高校和周边的商场拓宽出租渠道,很快就建立起一个市场网络。“黑大D区、中等装修、包水电网费、情侣免谈”都是房子的卖点。
以每间房8个小屋、每屋800元“保守估价”,这种房子一个月能赚6000多元,年收入7万余元。除去改造房子的材料费和人工费,空调、桌椅、床柜等约2万元的“简装”成本,以及水电网费、卫生费、管理费等,每间房年净收入约5万元。
为了进一步扩大“版图”,张俊龙特意跑到北京和上海考察群租市场。他已经拥有18套房子,靠租房赚了足有两百多万元,最大的心愿是年底突破25套。“市场非常火,几乎没有空置期,连春节都是满的。”张俊龙说,“我们这半年来基本不需要在网上宣传了,做出专业和口碑了。”
苏杨心有不甘。当年张俊龙样样不如自己,如今自己却混得要“寄他篱下”。他将自己那套板整的阿玛尼西装小心翼翼收进他的拉杆箱里,带着醋意对我们说:“同学聚会时都说,他读了四年大学,就干这个了?他也就这命儿了,再说他也住群租屋……”
保守估计,“黑大D区”靠这种群租发家的“二房东”足有上百个。正是苏杨、林鲍鲍这种怀揣梦想、带着心气儿、房租几乎占到月收入三分之一的年轻人,撑起了这片庞大的、摸不清轮廓的“高端群租”市场。
张俊龙已经很少亲自出面,每天吩咐手下提着一大串贴有编号的钥匙,开着摩托车穿梭在高层小区之间,带着那些神情骄傲的求职大学生或是年轻小白领四处看房。
身在这里,却感受不到这里
沉默与隐忍溢出眼眶,和外面的世界——城市的坚硬和无所不在的孤独——形成对视。
我们的同屋、28岁的朱琳已经考了4次研。她原本坎坷的故事被林鲍鲍三言两语“高度精炼”了:“她家里让她回镇上嫁人,她不干。之前在福顺尚都住群租,那儿外国留学生特多,交了个韩国男朋友……后来那男的回国了,严重影响到她考研的心情。一气之下,她就跑芳洲园这边来了……”
中秋小长假,群租屋里的“室友”基本都在,房间纷纷敞开,但无人多言。隐约听到朱琳在讲电话:“我在这边有许多朋友,大家都住在一起……安全、放心,大家互相照应呢……吃月饼了,妈你呢?”
这个听起来无限温馨的故事,真实“版本”却是,虽然是一屋子人,但彼此基本不沟通,甚至互相有戒备。“自己房间里的泡面、零食和钱包里的钱少了一两百元,是常有的事儿。”林鲍鲍说,“大家作息时间和生活习惯不同,有的加班回来晚,有的半夜了还在大声讲电话,有的整夜看电视剧……有人床上都是零食渣子,脏衣服堆满盆也不洗……我能明显感觉出周围邻居看我们的异样眼神。
人家不乐意跟我们说话,有时候都不愿意跟我们坐一趟电梯……”
心直口快的林鲍鲍花了一年多时间,才算是与做推销工作的苏杨、考研的朱琳、老家巴彦的大厨周传旺、考律师资格证的陈志卿、待业的杨渊慢慢相熟起来。至于“女汉子”,“那注定是个传说”。
周传旺可能是这间房子里收入最高的。“他就在附近的餐厅工作,一个月赚四五千元吧。”林鲍鲍提起大厨就乐,“他每天什么愁事都没有,吃了睡,睡了吃……有一天他跟我说,在哈尔滨住了十几年了,属这儿住得好,胖了十多斤。”
毕业三年间,杨渊换过3份工作:票务公司文职、电子产品销售、行政管理,每份工资不过一两千元。他一直想进入一家外企,从事外贸工作,但不得要领。收入上不去,连四五百块的房租都一度成了问题。
陈志卿班上的同学,有一多半挤入北上广。他坚持守在哈尔滨,为了避开北上广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激烈的竞争。“我也不知道这样的选择对不对,走一步算一步吧。”他想了想,“其实,哈尔滨的生活成本根本不算低。”
在朱琳的人生概念里,爱情是唯一能让她走出“贫民窟”的筹码。但“面包”最终灭了爱情,也几乎摧毁了她所有的念想儿。平日里,她不是外出打短工,就是努力迫使自己静下心备考。“现在谈恋爱,你不可能指着男朋友全给你花钱。”林鲍鲍说,“就算不买衣服,两人吃个饭、看个电影,这一天下来的恋爱成本少说百八十元吧……恋爱谈下来了,然后呢?结婚不?”
足够“热闹”的房子里,就这样唯独少了人的声音。沉默,更像是黑色幽默式的“抱怨”:他们几乎没有娱乐,也没有交际,彼此难以融入,更难以融入这座城市。他们甚至极少带外面的朋友到小屋里来。即使是中秋小长假,他们基本上只待在房间里上网、听音乐、吃饭、睡觉……这些事情不需要花钱。
最后一根羽毛
有人一住就是三四年,有人住了几天便离开。而无论是出人头地还是头破血流,小屋都是他们身上的最后一根羽毛,寄藏着他们内心深处对生活最本能的想象与期望。
在这种房子里住久了,即使是凶悍的“女汉子”,平日里的动作也习惯了轻手轻脚。她每天花在化妆上的时间至少半小时,穿质地很好的衣服,微端着双肩,默默走到门口,再慢慢穿上好看的高跟鞋。
这种微端的双肩,几乎是所有习惯在狭小空间生活的人所特有的动作。
周传旺的老家在农村。如今,他在大城市出息了,已经在哈西置备了一套房,打算把父母接过来,再娶个老婆。看得出,他对活泼开朗的林鲍鲍很有“意思”:她幽默聪明,他喜欢;她穿时髦的衣服,他喜欢;她拎一款PRADA的小包,他即使完全不懂名牌,也喜欢……
林鲍鲍对他的感情,准确说是“感激”。“我跟他是不可能的。我是个正经八百的大学毕业生,是知识女性。住在这儿也只是暂时的。再说,我父母也不会同意。”
尽管寄住在这样的小屋里,纵使月收入有限,他们穿着讲究,买苹果电话和平板电脑,所有能看得见的,并不吝惜花钱。“苏杨9月初去了趟香港,你看到的那套阿玛尼就是在香港买的。”林鲍鲍对我们说,“这个土鳖,在香港买了三箱名牌衣服回来,把一年的钱全花光了,哈哈哈,结果回来发现,箱子根本没地儿放!”
“但,我理解他,他并不是拜金。”林鲍鲍收起笑容,突然说。
大部分“蚁族”在全国的大中城市里从事服务性行业。“就用一句话总结吧:你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却过不上一个体面的生活。”林鲍鲍说,她有很多在北京打拼的同学,坐着飞机飞来飞去,住的是高档酒店,接触的是奢侈品牌,见的客户全世界各地都有,气派得很……下班回来,却是在只有几平方米的群租房里。没有咖啡,没有红酒,没有地毯……场景和角色实在很难转换,甚至不敢回家了……
但是,很多坚持下来的姐妹们最终赢了——搬出群租房,进了宽敞明亮的合租屋,有的买了房子,还有的嫁了人。
这种励志故事特别能支撑林鲍鲍。明年,她将会成为她们中的一员。她已经在哈尔滨积累了多年的工作经验,对未来的北京生活充满信心。“在这儿,恐怕也是一辈子买不起房,还不如去大城市闯闯……到了北京,肯定还要群租一阵子吧……那我不可能永远靠租房活着吧。”
朱琳常常突然神经质地问林鲍鲍:“你说,我们这帮人是不是有病?”在她的概念里,北京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蚁族”?答案很简单,因为每个渺小的“蚂蚁”都以为自己能有“破茧成蝶”的一天,即使他们现在的事业舞台和现存的上升渠道注定了大多数人会贫瘠一生,但每个“蚂蚁”都以为有一天能够搬进钢筋水泥筑成的小火柴盒里,给自己的小孩自豪地讲述奋斗史。
“留下,就有机会;奋斗,就一定能成功。即使只有1%的机会和希望,也会换来200%的斗志与期待。”
这句话,曾经被朱琳抄到考研教材的扉页,而现在,她的“窗子”正在不知不觉间关闭。她依然是每一间房子里的陌生人。她甚至每一天都筹划着如何搬离这个闷罐头似的世界,但是目前,她没有与这座城市、与未来、与命运讨价还价的筹码。
“未来”,成了一些人无法轻易碰触的内心的匣子。
好在,他们还能住得起这样“体面”的小屋。在他们的世界里,小屋无论是跳板,是港湾,还是终点,都是能够掩饰疼痛的一根华丽的羽毛。
“逃亡者”
我问朱琳最后一个问题:“你想不想回家?将来回不回家?”
陈志卿三句话不离自己做律师的梦想。他读了很多书,国家政策、公共事件、互联网,都能侃侃而谈。现在的生活,对他而言更像是一种历练,“就当体验生活,创业,哪有不吃苦的?”
然而,对于像朱琳这种不断经历跌撞、却不肯回乡的人来说,所谓的创业、人生、未来与梦想,已经渐渐无法让她提起那口心气儿。
张俊龙丝毫不担心哈尔滨有一天会像北京一样,对群租全城严打。随着更多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那些被称作“蚁族”的群体依然会迅速膨胀,往更多角落延伸。群租也并非北京所特有的问题。上海、广州有之,香港、东京有之。阶段性的治理和简单的禁止往往被证明基本无效。一阵风过后,群租者再次回流。
他们更像是“逃亡者”——来自乡村或是小城市,接受了现代知识教育,却无法再回到家乡,但在城市又不能得到有价值的就业和有质量的生活。陈志卿告诉我们,他的很多同学曾努力“逃离北上广”,最终,又很快“逃回北上广”。而那张往返程的票根,是两个城市对他们下达的“不适宜鉴定书”:大城市是堵的,贵的,拥挤的,奢侈的,排斥人的,是人家的北上广;而老家,是落后的,是势利的,关系的,拼爹的,依旧是别人的。
生活为何变为如此?他们的文化、道德与生存为何变得如此?即使,他们在大城市搬到了有窗子的、宽敞一些的房子,或是买到了房子,一切就都改变了吗?他们就获得了权利,就有了居住的地方,有了体面的生活,就老有所依了吗?
中秋节过后,就在我们已经掌握足够素材,准备“收线”并离开群租屋时,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桂松伟打来的。他对此前以“租房”名义到处看房的我们始终“念念不忘”:“姐,我看你们人都挺干净的,住在这儿我也放心。我老婆眼看就要生了,着急用钱,房子你还租吗?给多少钱都行……”
【尾声】
离开群租屋后,听说西典家园的房租涨势凶猛,我们于是再次以“蚁族”的身份去看房。“其实也没涨那么凶,一间房多三四十元吧。”一个二房东摇晃着一大串钥匙,显得不以为然,“也就是因为附近的万达新开业,很多白领住进来了,房主要抬我们的价儿……”
西典家园小区内的路十分坑洼,很多路灯坏掉了。我们坐在二房东的摩托车上,一路颠簸到处“看房”,甚至连对面过来人的脸都分辨不清。
小区门外,早已人声嘈杂。十余平方米的快餐店前排起一条长龙。租房客们涌出小屋,心满意足地提着6元晚餐——两荤一素带一个汤,打包带回。
年轻的保安告诉我们,他很喜欢在那里工作。“我没读过大学,这里就跟大学宿舍似的,年轻人多,热闹……”
在那里,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又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寒来暑往、日夜轮回,那些透出微弱灯光的群租屋里,进出的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