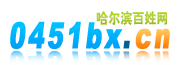|
||||||||
|
|
||||||||
|
 |
 |
 |
 |
在北京的一家很文艺的书店买了一本很文艺的书,付款时,从书中掉落了一张淡雅的书签,弯腰拾起,书签的右上角用极小的字体写着博尔赫斯的那句有名的诗句:“我心中暗暗猜想,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心里温暖地荡漾了一下,突然很想写写那些曾让我安静坐下来的“天堂”。
母亲年轻时在新华书店工作,父亲爱书,因此常去书店,便在那里遇到了母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存在本就与书有关,我若不爱书,便成了一种叛逆。好在我在父母的引导下,果然成了爱书的孩子。
年幼时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在假期里跟着母亲上班,在不许碰乱新书的规则之下,我被允许在书店的书库里做作业。印象中的那个书库温暖而干净,成捆的新书包裹在厚厚的牛皮纸中,散发着让人着魔的铅字味道。我最终还是忍不住去触碰,小心翼翼地在一排排书架间挪动脚步,寻找自己喜欢的书,然后拿到白炽灯下小心地翻看。因为深知那些书并不属于我,因此从不敢用力翻页,更不敢留下折痕,每次都全凭记忆找到自己上一次读到的地方,后来,这个习惯就一直保留了很多年。那真是一个个奇妙的假期,每天从书库中走出时,十几岁的我竟能感到自己成熟而有力。那个书库就是我印象最早的图书馆。
第一次身处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是在上中学以后,县城初中的走廊尽头有一间小小的图书室,入学参观时老师允许每人拿一本书坐下来阅读,我激动地站在高高的书架前,决心选一本最值得阅读的书,由于太珍视这一选择,竟始终犹豫不决,在书架间走来走去,直到老师宣布大家离开。对图书馆的依赖从此日渐加深,从中学到大学,每每遇到所谓的挫折时,便立即坐进图书馆里找一本“有力量”的书来读,大学四年,手写的图书证因此用光了几本。
图书馆渐渐离我远去,是在上班以后。依然还是喜爱买书,只是在读书时缺了几分专注与激动。虽然还保持着睡前看书的习惯,但再好的书也难再有战胜困倦的力量,书中的内容记得模模糊糊,记得最清的却常是入睡那一刻书本重重拍在脸上的疼痛。
决定要在英国读书是十二年前的事,让我萌生这一想法的地方就是利兹大学的布莱德顿图书馆。那一次我是去英国旅行,老沈带我参观大学的图书馆,我们走在那座古老的圆形图书馆的二楼,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一个女孩子坐在两排书架间的地上专心地阅读,脚边散落着图书,夕阳从她身后小窗口射进来,斜照在她脚前地毯上。我就这样看呆了,在心里郑重地对自己说:“我想要这样的生活!”
2003年我再去英国,身份是老沈的陪读,也因此在利兹大学得到了一张临时读书卡。我们就在布莱德顿图书馆主楼的对面租了一间学生公寓,我因此每日出入那里学习,那张只能读不能借的临时图书证,被我揉搓得柔软而破旧。我经历了布莱德顿图书馆的完整四季,开学之初的兴奋、考期的拥挤和假期时的清冷。我坐在一群学生中间,拿着很初级的英语书籍阅读,抬起头看那些学生时,心中总有一种隐隐的忌羡,我太想成为他们了,只能再把头低下,沉浸在并不流畅的阅读里。第二年我终于如愿成了学生。那年9月,领了学生证,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布莱德顿图书馆,在那个被我踏过了上百遍的电子门前,我第一次用真正的图书证对准了感应口,旋转栏杆“嘀”地一声为我打开时,我竟然十分煽情地掉下了几滴眼泪。
利兹大学的图书馆里有我最爱的四个角落。
至今还记得第一次仰望布莱德顿图书馆大厅穹顶时所产生的联想,那不像图书馆,更像一座教堂。那种高度,那种从菱形窗子射入的自然光,会让人在仰望时心胸顿然开阔,有时还会引发一种隐隐的、想要有所作为的野心。因此,大多时候我会在大厅里寻个座位坐下,在那里低头读书,在那里抬头思考。
布莱德顿图书馆圆形大厅的周围还环绕着许多小巧的图书室,像若干个立体的扇面,包裹着大厅。那里厚实的木书桌也许真的有上百年的历史,磨损了的圆头铁钉和已有些龟裂的墨绿皮革显示了它不凡的高龄。这些小室大多归属法律和哲学部,烫金的书脊和老书的味道时刻提醒在这里安坐的人们学术的神圣与尊严。如果足够幸运,我可以在人不多的日子单独拥有这样一间小室,斜依在木椅上读书,不知不觉,一天便会过去。
布莱德顿图书馆的地下室,据说拥有全欧洲最大的中文图书馆藏。那里可以找到古龙和金庸全集,甚至可以查到中国某些不知名小城的《县志》。我常常在心情最烦躁的时候去那里读书,从狭小的旋转楼梯走下去,围着巨型书架一圈圈地查看,哪怕只是看看令人怀念的汉字的样子也好。那里很少有人光顾,只有最需要安静的学生才将自己深藏在这里,以图书为壳,营造与世隔绝的思考空间。
利兹大学的另一座图书馆叫“爱德华·鲍埃欧图书馆”,那里的藏书量不在布莱德顿之下,但以短期借阅为主。我最喜爱位于第八层的自由区,那是图书馆中唯一一个可以吃零食、大声讨论和打电话的地方,虽然设在图书馆的中央,但有自由市场一样的火热气氛,每到下课都坐满了小组讨论的学生。最爱那里竖立的一块块大白板,专供学生随意涂抹之用。在这些白板上,我学会了英国人的一种叫“头脑地图”的思路清理方法,将头脑里的“一团乱麻”画在白板上,再一点点地勾勒出头绪“装”回大脑中去。
大学图书馆的海量学术藏书盖过了利兹市中心图书馆的风头,在利兹生活的八年里,我在市图书馆借书的总数不到十本,但那里有着皇家气质的艺术咖啡厅却让我时刻想念。那恐怕是我在英国见到的最大、最古老的咖啡厅,从墙壁到顶棚都由图案精美的瓷砖镶就而成,走进那个艺术感与历史感交会的空间里,时常会觉得恍惚,惊诧间会忘记来喝咖啡的初衷,我总是先满怀敬畏地观摩一番,才会在咖啡的香气中恍然大悟。由于空旷,杯盘撞击的声音会产生回响,那声音竟也格外清脆悦耳,受了这种视觉、嗅觉与听觉的多重引诱,很多人借了书,并不想回家,也不愿留在图书馆中阅读,而是走到这里,叫一杯咖啡,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消磨上小半天的时光。
英国的每个小镇,也都有属于自己的图书馆,它就像教堂、酒吧和超市一样,是人们生活的必要元素。图书馆也反映了一个小镇的“年龄”与“性格”。
莫雷小镇的图书馆就在我新公寓的斜对面,从客厅的窗口向右看,就能看到那个低调的小楼,与周围的普通民宅并无区别,乍暖还寒的英国初春,总是笼罩在一种青苔色中,雨滴中似乎都渗透着一种淡淡的灰绿,在这样的天气里看莫雷图书馆,真有几分难以言状的没落。
第一次去那里看书是因为家里的暖气坏了,我带着电脑坐进那间狭小的阅览室,与来此看报的老人共用几张大桌子,那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安静,我甚至不敢敲击键盘,因为那声响竟有些让人心惊肉跳。我不忍打破老人的这份宁静,半个小时后,借了几本书匆匆离去,从此放弃了这个离家最近的图书馆。
与之相比,更喜爱奥特雷小镇的图书馆,我工作的那所中学就在图书馆附近。图书馆很新也很大,现代的钢架结构,绛红色的地毯总会让人心生快意。天气好时,老沈会开车送我上班,然后在奥特雷图书馆写他的博士论文,直到我下班再接我回家。老沈说他不用看手表,当图书馆的地毯上突然多了很多趴在地上看书的孩子时,他就知道,他老婆工作的那所中学放学了……
回国后,钱包里又多了两张图书卡,一张是省图书馆的,另一张是国家图书馆的。搬到一个新地方,就先到那里的图书馆坐坐,已成了我的一种习惯,因为我相信那里坐着那个城市最沉静的人,他们营造的氛围和磁场,会让我忘掉琐碎、沉下心来。心中也暗暗盼着儿子快快长大,也带他在这样的氛围中坐一坐。如果父母真的可以传递给孩子某种喜好,我希望这种喜好是阅读。我希望他无论身处青春的躁动、中年的纷杂,还是年老的孤寂,都能找点时间,安坐下来,手捧一本爱书,用心品味那种静谧的激情。这样的人,无论成败贫富,都是可以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