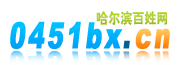|
||||||||
|
|
||||||||
|
专栏主笔 毕蔷
谋生不易,世界上任何角落都是如此。因人而异的,有时是那些往返于“谋生路”上的风景和心境。上班的路上快乐,那我们还满意那份工作;下班的路上快乐,那我们还热爱眼前的那份生活。人生的奔波,循环往复,无非如此。
读研时,在一个叫布莱姆雷的小镇打工。那个小镇离利兹很远,去往那里的公共汽车只有市中心的汽车总站才有,从那里出发坐半个小时的车,再走十分钟才能赶到我打工的中餐馆。从利兹启程时是下午3点,公共汽车上几乎没什么人,只有温暖的阳光充满整个车厢。
车站的隔壁就是利兹市最大的露天市场,夏初的时候,新鲜上市的大樱桃只要2英镑就可以买上满满一大纸袋。因此我总是手捧着这样的美味上车,挑选一个迎着阳光的位置,幸福地眯起双眼,一边观赏窗外的美景,一边满足地吃着怀里的樱桃。因为那时的我是个纯体力劳动者,所以常能自然的将那袋樱桃的美味与即将付出的劳动所得联系起来——“工作一个小时,可以换得两袋半这样的樱桃”,我傻傻地想,幸福的心安理得。
下工时就是半夜,再也没有回利兹的公共汽车了。老板向老板娘申请,要开车送我们三个打工的学生回利兹。他吹着口哨把那辆几乎没怎么动过的红色小“尼桑”开出车库,车子启动时,他兴奋得像个孩子。我们都知道:老板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脱离老板娘视线的时刻。这个家庭据说是布莱姆雷镇的首富,他们经营着小镇里唯一的中餐外卖店长达20余年,可作为老板兼大厨,这个温柔而懦弱的香港男人全年的休息日不足五天,每个月从老板娘那里领来的烟钱却少得可怜。在车上,老板会很奢侈地吸一支烟,说一些并不好笑的笑话,他那辆拥挤的小车里温暖而愉悦。有一日我们问老板:“有一天不做外卖店了,最想做什么?”他深深地吸了口烟,缓缓地说:“抱着鱼竿,看月亮……对,就是这样喽……”我们都无话可说。没想到,一个富人的理想就这么简单。
后来老沈买了车,老板每周两次行驶在利兹与布拉姆雷间的快乐也被剥夺了,而关于老板退休的谈话也自然再无下文。在老板娘锐利的目光下,我们与老板的交流越来越少,只能看着他微弓的身影在厨房里沉默地忙碌。那是9年前,老板已经60多岁,不知道现在的他是否得到了想要的鱼竿,看到了他想看的月亮。
那段夜半回家路上的幸福,属于老板那样辛苦劳作的富人,也属于我们这样没心没肺的穷学生。坐着老沈的车回利兹,我的手中总是紧紧攥着老板娘给我们发的当日工资,心里说不出的踏实。从布拉姆雷回利兹要开过宽敞开阔的M1公路,再经过一段完全无路灯的B级公路,冲过那条弯曲的小路,就会看到利兹城在很远的地方闪烁,有身处其中时难以觉察的繁华。有一段公路的地势很低,初冬的深夜常会浮起一片浓雾,那是一种超自然的浓雾,汽车的雾灯直射雾里竟无法穿透,只能再反射进视野,就像露天电影院支起的巨大幕布……
最辛苦的上班路是在H中学教书的前两年。从我所住的利兹阿姆雷区到奥特雷镇,需要乘2个半小时的公共汽车。冬天,我必须在早晨5点50分之前出门,只有这样才能赶上市中心那辆去往奥特雷镇的X84线,好在这路汽车在早晨被征用为H中学的校车,能从市中心一直驶进H中学的校园。早上6点前,英国的冬日都是漆黑的,昏黄的路灯照在灰白的石子路上,行人的鞋跟与石子路在小巷里撞出清冷的回响。我太困了,总是在车上沉沉睡去,好在终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8点50分,第一节课开始了。常有学生调皮地告诉我:“毕女士,我早上就坐在你的旁边,你睡得很香……”我也假装调皮地看看他们:“那我有没有打呼噜?”说话的学生还真的认真地想了一想:“那倒没有……”
与上班的路相比,下班路并不显得漫长。在奥特雷小镇中心的汽车站等X84时,我有时会坐着给学生批作业,再抬头时,会看到毛茸茸的小脑袋好奇地向我张望——与我一起等车的学生很想知道:老师会给什么样的作业打“Excellent”(优)。
X84都是双层巴士,最喜爱的是上层的第一排,将双脚搭在面前的护栏上,视野与内心的开阔都无法形容。上层会感到更多的摇摆,像一只巨大的摇篮,安抚着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有行至窄巷时会有树枝突然敲打车窗,才将我拽回到现实之中。
最怀念的是坐火车下班的路。
上学时曾为一位牙医的一双女儿做家教,每周只上一节课,回家时就由孩子的母亲送我到他家附近的火车站坐车回利兹。车站很小,只有火车道边上的两把长椅、一块张贴着火车时刻表的布告栏和一座古老的大钟。
坐在那座钟下等车,只有电影中才有的、淡雅的文艺味道。站台上常常只有我一个人,车厢内也往往如此。几个月后,一同等车的人多了一个抱着吉他的英俊少年。我们坐进同一车厢,火车启动后,他总会先对着玻璃窗沉默一会儿,然后抱起吉他,一曲曲地弹奏优美又有些感伤的曲子。那旋律纯洁而流畅,让坐在另一侧的我内心瞬间融化。我们的目光偶尔相遇,彼此默契地点头微笑。我闭上眼睛,想象着那列火车穿过牧场,跨过小溪,一路悠然,驶入利兹,我和吉他少年在那里点头告别。走出车厢便是另一番景象,疲惫了一天的上班族在利兹的火车站会聚。长风衣、破旧的牛皮公文包和形色各异的耳机。耳机里的音乐将眼前同样的风景,在不同人的心里演绎成不同的故事画面。人们快步如风、擦肩而过,走出站口,走回各自的人生故事里去。
后来我学会了开车。那时,我已在英国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摇摇晃晃地遐想了5个年头。我自己的第一辆车,是一辆黄色的大众高尔夫,卖给我时,我是它的第十一任主人。
第一次开老“高尔夫”,是去利兹大学上班,到了那里才发现停车位并非那样易得,眼看要到上课时间,为了避免教学事故,我咬牙把车停在了双黄线上。下班后,果然看到黄色的塑料口袋明晃晃地贴在车窗上,罚单上赫然写着70英镑(按时付款享受半价)。此后我都十分小心,渐渐学会了“踩”着最高限速开车,也给寻找停车位留下足够的时间。那张罚单成了我在英国的第一张、也是唯一的一张罚单。
老“高尔夫”的暖风热得很慢,冬日在晨曦微露时启动车子,到迎着朝霞在高速路上狂奔,保温杯里的奶茶总能从滚烫喝到冰凉,我那头湿漉漉的头发总是先被冻硬,然后蒸发成蓬松干枯的发卷。尽管如此,我热爱这辆忠诚的老柴油车,因为许多个清晨,它为我争取了额外一个半小时的黄金睡眠。
最难忘的是每个去哈罗盖特城上班的星期二,我在那里有两节大学的夜大班要教。那是个全英著名的花园城市,但每次驶入哈罗盖特城时,那里的美景早已湮没在夜色之中。时常犯傻的导航系统会将我导入无人的田野里,左边是农田,右边是山坡,窄小的石子路只能容一辆车穿行,如果有两辆车对向行驶,其中一辆必得暂时斜倚进农田的边缘。夜深时,常有野兔或小狐狸一样的小动物突然从车前穿过,恍惚间会看到两只眼睛在漆黑中反射出刺眼的光。那并非最可怕的场景,最可怕的是瞄一眼一片漆黑的倒车镜所产生的无限联想。后来就有了同事米娜同行,就是那位我曾经提到过的、常爆粗口的女博士。再遇到小狐狸挡路时,就会有米娜和我一起尖叫,她还会夸张地高喊:“我靠!这TM是什么生物?”有了米娜,似乎被外星人劫持都不那么可怕了。
送米娜回到她在利兹大学附近的公寓是夜里10点,再驶入我住的莫雷小镇是10点20分,街角的“多米诺比萨”尚未打烊,我常会坐在柜台前等一张刚出炉的小比萨,厚厚的双倍奶酪在装入盒子时依然鼓着热泡儿。这是我一天中的第四顿饭,我需要能量,那一天,我讲了9个小时的课,开了3个小时的车。但是第二天,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躺在床上眼望天棚一整天——这正是教师这个职位对于我最“致命”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