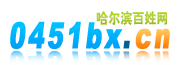|
||||||||
|
|
||||||||
|

江苏淮安市淮阴区杨庄村,正在田里放羊的农村老人。 本版均为资料图片
■ 关注焦点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故事:除夕夜,河南邓州某村,一名近百岁的老人因无人看护,在家中被火烧死。
事件让其儿孙陷入舆论漩涡。一个事实是,儿孙也有儿孙要养。在土地产出显得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能满足老人“有碗饭吃有间房住”基本成了这个村庄赡养老人的高标准。
终生劳作,自食其力,需要老而弥坚的身体;若是子女“不孝”,晚景难免凄凉;而对于那些没有子女的五保户,一切更不在掌控———这是邓州李庄的养老困局。
不过,年轻人知识的增加和观念的改变,也正改变着这个村庄。
李庄最后一个小脚老太走了,97岁。
在河南邓州市十林镇,对80岁以上老人的辞世,叫“喜丧”。
但任何一个知道张阿婆死因的人,都不会想到“喜丧”这个词———今年大年夜,她独自烤火时,棉衣被引燃,不得解脱,活活烧死。
没人听到她的呼救声。她遗下成灰烬的衣服,和发焦的身体。
邓州市,李庄是最普通不过的一个村子,张阿婆是最普通不过的一个老人。
传说,李庄的祖先是在明朝初期从山西洪洞县,在大槐树下编组迁徙至此。600多年过去,村民们用上了“山寨”手机,骑上了杂牌摩托,但土地和生育,仍与600多年来一样,是此地居民生存的两大主题。
在土地上流了一辈子汗,生下一大群儿孙后,农民成了老农民。而对老农民来说,养老,是一个比种地更棘手的难题。
至少,张阿婆的死,让李庄每一个老人忍不住叹息落泪。
大年夜的火灾
能让老人有碗饭吃,有张床睡,也就是村里人理解的“赡养”了
要是张阿婆身上的火没引燃柴垛,她会死得更沉默。
目击者说,大年夜7点半左右,邻居发觉张阿婆家院子起火,赶忙冲过去救火。
一二十分钟后,燃烧的柴垛被扑灭。
大家在屋里屋外都找不到张阿婆,正着急,有人发现了一具尸体,蜷缩在柴垛不远处,衣服和头发已成灰烬,皮肉焦黄。
大家推断是她烤火时引着了身上衣服,出门求救时又引燃了柴垛。
“她一直怕死了被火化,没想到还没死就被火化了一回。”张阿婆六十多岁的大儿子痛悔自己不在场。他当时串门去了。
这是个没有院墙的院子,张阿婆住在右侧厢房,大儿子住在中间房子。她的两个孙子,则住在300多米远的村西头。
一个事实是,在李庄的老人中,张阿婆属于晚景相对好的。至少,她吃穿不愁。每到吃饭时,总有后辈从村西给她端饭。
不过,她97岁了,这个冬天又过于寒冷。旧瓦房内,她不断往火堆上加柴。
出事前一天,腊月二十九,同村的洪东花说,她几天前去张阿婆家串门时,发现她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旁边的柴禾不知怎么引着了。“要不是我们恰好碰到,她就被烧死了。”
洪东花没想到,张阿婆真的被烧死了。
张阿婆的死讯,让村里的老人们普遍感觉悲哀和愤怒,也让她的儿孙遭受指责。
“为啥孙子不让她住一起”,“快一百岁了,还一个人烤火?”,“饭端那么远,早就不热了,能吃吗?”……
对于村里人的指责,两个孙子也知道一些,他们沉默。
“不关小辈的事,都是我的责任。”他们的父亲抹着眼泪说,两个儿子农活都很繁重,都要挣钱养活一家老小,“不可能天天看着奶奶”。
事实上,张阿婆的两个孙子曾讨论过,由老大赡养父亲,老二赡养奶奶。最终两个孙子都在管奶奶吃饭。
在李庄,能让老人有碗饭吃,有张床睡,也就是人们理解的“赡养”了。
跟村里其他老人一样,张阿婆生前也经常夸耀自己的儿孙。
四十出头的大孙子两年来去过外地打工,但因没有技术,闯荡先后失败。回到村子后,他沉默了很多。
二孙子一边种地,一边在村里建筑队做泥水匠,一天能挣几十块钱,也非常忙。
孙子们也有儿子,老人慢慢淡出生活的中心。
“不服不行呀,我也六七十了。唉,这人一老,就跟面前有条深沟一样,你不跳,这小孩子们一茬接一茬往上长,都在催你跳呀……”正月初二,张阿婆的大儿子站在棺材边,与族人交谈。
张阿婆的棺材是早就备好的,沉甸甸的香椿木。
活到老,干到老
“坐到屋里啥活儿不干,光知道吃饭,那不是自己扇自己老脸吗?”赵喜菊笑
张阿婆生有一女三男。女儿远嫁到几百里外,二儿子常年流浪在外,三儿子八年前自杀。
此前20多年,她一直与三儿子相依为命。三儿子自杀后,她跟大儿子一起,靠两个孙子供养。
儿孙多劳力就多,使她早在六七十岁时就不用下地干活了。在人均土地2亩半的李庄,只要身体允许,七八十岁的老人还得下地劳动。
何况,李庄四分之一的村民都外出务工了,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他们把孩子和土地留给了老人。也使得老人成了难以卸掉套具的老牛。
据村干部估计,李庄至少有30多名留守儿童。他们都靠爷爷奶奶照顾,学习成绩几乎没有上优秀线的。
大人们也不十分在乎这个。众所周知的是,大学生一年比一年难找工作。务农和打工的门槛却很低。
不过,务农是没有退休时间的职业。赵喜菊今年78岁了,除了不拉车耕地外,拔草、施肥、浇苗、薅花生……跟年轻人一样劳作。
老伴小她4岁。过年时,外地的三个女儿会给他们寄点钱,而两个儿子,还没有开始赡养老人的打算。
“我身体好着呢,让我坐到屋里啥活儿不干,光知道吃饭,那不是自己扇自己老脸吗?”赵喜菊笑。
赵喜菊老两口独户过日子,有饭吃,有钱花,让不少依附于子孙的老人颇为羡慕。不过,并不是每个人到了78岁,一顿饭还能吃上两大碗饺子。
身体好,才能活得有尊严,在李庄是条真理。
“养儿防老”靠不住
未经允许吃了一个苹果,卓婆婆被指责“偷吃”,并就此扫地出门
所谓“养儿防老”,其实是靠不住的,比如卓婆婆。
她有5个儿子,但跟儿媳相处都不好。去年冬天,她未经允许吃了某儿媳一个苹果,被指责“偷吃”,并就此扫地出门。
她没地方睡,去找分居的老伴,老伴说,“我都快没人管了,你少牵扯我”。冬夜,她在村里转了一圈,几个儿子家的门敲了个遍,然后向村外走去。
庄稼地头,有地方堆着玉米秸秆,她钻进里面,和衣而睡。不多时又被冻醒,她再次转回村里。
这还仅仅是一张床的问题。疾病,更是可怕。
在李庄,老人一旦发现癌症等绝症,其存活期一般不超过一年。儿女坚持要给治疗的,凑点钱能做个手术。倘若儿女财力不济,或不想破费,只能到卫生所买几瓶止痛药片,延续性命。
在不少老人看来,患癌症速死,还算体面。村西姚婆婆中年就瘫痪,大儿子嫌分家不公,对她不管不问。
那是十几年前,小儿子因超生东躲西藏,仅小儿媳在家支撑,姚婆婆饥一顿饱一顿,基本的卫生都没人做。
当时,姚婆婆有六十多岁。一年夏天,她女儿回娘家为她洗身子时,发现一些地方生蛆了。“活人生蛆”之事由此传开。不过,她的境况,并没因此改善。
七八年前,姚婆婆去世,结束了她“寿长多辱”的一生。
几百年来,李庄的人们一直靠天吃饭,他们的行事,无不源自农民糊口的本能。
年轻人好吃懒做并不可怕,大不了娶不到媳妇。但一个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多半要被视作累赘。而除了老亲旧眷,不会有人去谴责那些所谓“不孝”的年轻人。
并不稳固的家庭
20年来,李三爷给村里的父子间,出过不下十份“活不养、死不葬”的“字儿”
十几年来,李庄离婚的夫妻不超5对。但说这里的家庭结构多坚固,也未必如此。
李三爷是村里比较贤达的人物。经常在红白喜事做个知客,场面上陪陪酒什么的。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做“出字儿”的见证人。
一旦有宅基地划分、借款、分家等事宜,村民不会找什么公证处,而是找中间人,大家商议一份协议,三方签字画押,叫做“出字儿”。
分家,向来是李庄兄弟不和、父子反目的危险期。大到一间屋子一处宅基地一头牛,小到一个老木箱或几把椅子,都可能催生一张断绝父子关系的“字儿”。
李庄没有因赡养问题闹上法庭的先例,有的,是“字儿”。
20年来,李三爷出过不下十份“活不养、死不葬”的“字儿”。一旦有儿孙怀疑老人分家不公,往往就要出字儿:老人可以将家产分与一个或几个孩子,剩余的孩子则不负责老人的生养病死。
上文中提到的赵喜菊,在十几年前分家时,为三间土坯房,大儿子与父母出了一张这样的“字儿”。尽管几年来两家关系已非常好,但那“字儿”并没有撤销,这或许更坚定了老两口自食其力的决心。
年初一,赵喜菊的大儿子去向张阿婆家人问候,很感慨,“想想以前分家,大家为几间烂房子争得鸡飞狗跳,何必呢?”
李庄父子“出字儿”虽不鲜见,但具体人数并无统计。事实上,老人们往往也只依靠某一个孩子赡养,很少有几个孩子轮流照顾的做法。
不过,让李三爷欣慰的是,近年来,兄弟分家发生纠纷的事情越来越少,一则大家书读得多了,都不跟他们文盲半文盲的父辈一般见识;二则,大家都出门打工挣钱,盖房子置家具一般自力自为,老房子老家具都看不上眼,也懒得争了。
相比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更牢固些,在晚年更能依靠。不过也不尽然。比如上文的洪东花,有三女两儿五个孩子。22年前,因她执意要供三女儿读书,惹恼了老伴儿,找人跟她“出字儿”分了家。
二女儿、三女儿,几百斤小麦,两间原本养牛的土坯房,归了她。“刚分家时,我感觉丢人呀,又生气,天天站在门前骂他。”直到有一天,14岁的小女儿说,“我在河边站了好几回,差点跳了,就怕我死了你可怜……”小女儿承诺,她以后赡养母亲,母亲没必要骂任何人。
洪东花不再骂了。过了十几年,小女儿历经艰辛,进入南阳市区一家工厂,成了“国家人员”,并与当地人结了婚。
洪东花那两间土坯房更破了,漏风进雨,墙体也越来越斜,邻居们都相信,若是对着墙跺一脚,那房子准会倒。
小女儿没有食言,一直让母亲去南阳。但洪东花的二女儿夫妇在北京打工,留下一对儿女让她照看。
“等老二从北京回来,我就去南阳了。这土坯房推倒算了,反正也快倒了。”夕阳下,洪东花笑了。
对两个儿子是否养老,她已不再关心。

青海农村,一名老人带着留守的孙子。
五保户的晚年
跟着妹妹的儿子住,五保户李瞎子的补助金,和一年的土地租金,都归妹妹家所有
在李庄,还有6名五保户;李庄所属的大行政村,一共有五保户和孤儿30多人。
五保户的标准是:没有儿女,年龄在60岁以上者。
他们一个月可以领70元的补助。
李庄的6名五保户中,5名仍旧下地干活。原因很简单: 70块钱只够天天啃方便面。
村干部说,各个村民小组为五保户名额,都争得厉害,但其实指标是上边定额的。
没人能预料到这6名五保户在不能活动后,将面临何种困境。不过,五保户李瞎子的现状,可以作为一个典型参考。
70多岁的李瞎子其实并不是瞎,他年轻时长白内障,眼神不好,人们叫他“瞎子”。
李瞎子很和气,青壮年时期逢大集体,他干活很卖力,人们都愿跟他搭帮。谁家有啥事需要帮忙了,喊他,没有不应的。
虽然他很招人喜欢,但因太穷,他没结过婚,成了老光棍儿。在他60来岁的时候,他听说白内障可以治,但需要很多钱,就“不治算了”。
当时,他正帮本家一个侄子看小孩。两个小孩都叫他“爷爷”,村里风传这一家要为他养老。当小孩到上学年龄后,人们发现,李瞎子又回到他的土坯房里,自己给自己做饭。
6年前,两间土坯房又被大雨冲塌,村里已无他的栖身之地,他移居五六里外的妹妹家,由外甥赡养。
他的五保补助金,和一年500块钱的土地租金,都归妹妹家所有。
他住在主房旁搭建的一个窝棚内,窝棚很小,仅容一小床。去年年底,一名村干部去探望,见被褥单薄,窝棚到处是缝,任由寒风进出。
“就不能糊几张报纸吗?”这名村干部颇感辛酸。
这个曾经乐天豁达的老人,早年因乐于助人而为众人所喜欢;在步入人生的晚景后,这个村子已慢慢遗忘了他。
他最后一次回到李庄,是在去年。邻居没有打招呼在他宅基地上盖了房子,他外甥开着手扶拖拉机,将他拉回村里,往宅基地上一丢,扬长而去。
对方急了,忙找人说和,最后补偿一千元了事。于是,李瞎子又被拖拉机拉回那个四面透风的窝棚了。
他的妹妹回过几次村子,找中间人讨要那两亩多地的租金。
之外,很少再有他的消息。不少年轻人甚至以为他已死了。
如果五保户没有亲戚收留,还可以住到养老院里。这个镇的养老院由一所公路边废弃的初中改建。
听说里面伙食还算不错。不过不到万不得已,没人愿意过去住。在老人们的概念里,一住进养老院,就意味着,等着老死。
生存与“防老”的继续
“不多要个孩子,我老了,谁养活我?”这是那些超生的村民最常见的理由
因过年有禁忌,张阿婆的下葬日期延迟了四天,到初六。
“三六九,顺风走。”这一天,李庄的年轻人开始离开村子,到远方去打工。
初六早晨,张阿婆也离开了村子。八个本家的青壮年抬着棺材,将她抬到她曾劳作一生的田野里,埋下。
子孙们大声或小声哭着,送葬的村里人也都流泪。
一个原本不属于李庄的人,告别了李庄。
此时,六十年未曾有过的旱灾正在持续。整个冬天,李庄没有下一场雪,甚至没有一场湿过地皮的雨。村外的麦苗,颜色越来越接近荒坟上的枯草。
活着的人们仍在为生存而奔忙。然而,旱灾却并没有引起大家的过多担忧。在李庄,仅指望农业,温饱是没有问题,但想盖房娶媳妇,则是“做梦”。
这里人均土地两亩多,两亩地一年至多净收入一千元,这仅相当于在南方服装厂半个多月的工资。
所以,人们不再把庄稼那么当回事了。
但生儿育女还得继续下去。李庄,不超生的家庭微乎其微,有女孩的人家想生个男孩,有男孩的人家还想再生个女孩。
那些超生的村民最常见的理由是,“不多要个孩子,我老了,谁养活我?是政府,还是你们这些干部?”
没人能圆满回答这个问题。除非可以证明李瞎子等五保户,正过着幸福的生活。
基层对超生也不再像十年前那么严了。在李庄,只要支付一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就可以生二胎了。
那么多的“社会抚养费”究竟抚养了谁,村民们也懒得过问。在这里,每一个日夜都显得那么平凡,鸡鸣犬吠中,数百名老人和孩子守着这个村子。
村里多数老人安于贫困,在生命最后的阶段,有碗热饭、有个暖被窝便已满足。而以此标准看,大多数老人还都能如愿以偿。
大年夜张阿婆之死,让李庄人更多地去注意老人的问题和他们的生活。
这个春节,村里老少提起张阿婆,无不叹息。
那些常年在外的年轻人们发现,老人们竟是如此脆弱,当你看见他们时,他们无所求地活着,看不见时,他们可能就永远离你而去。
事实上,伴随着学历和见识的增长,以及经济能力的改观,年轻人已开始改变和正试图改变村庄的生活方式。
能让生病的老人接受好的治疗,让年长者住上宽敞明亮的房子,是多数年轻人的愿望。
(注:因涉及家庭及个人隐私,村子村民皆为化名)